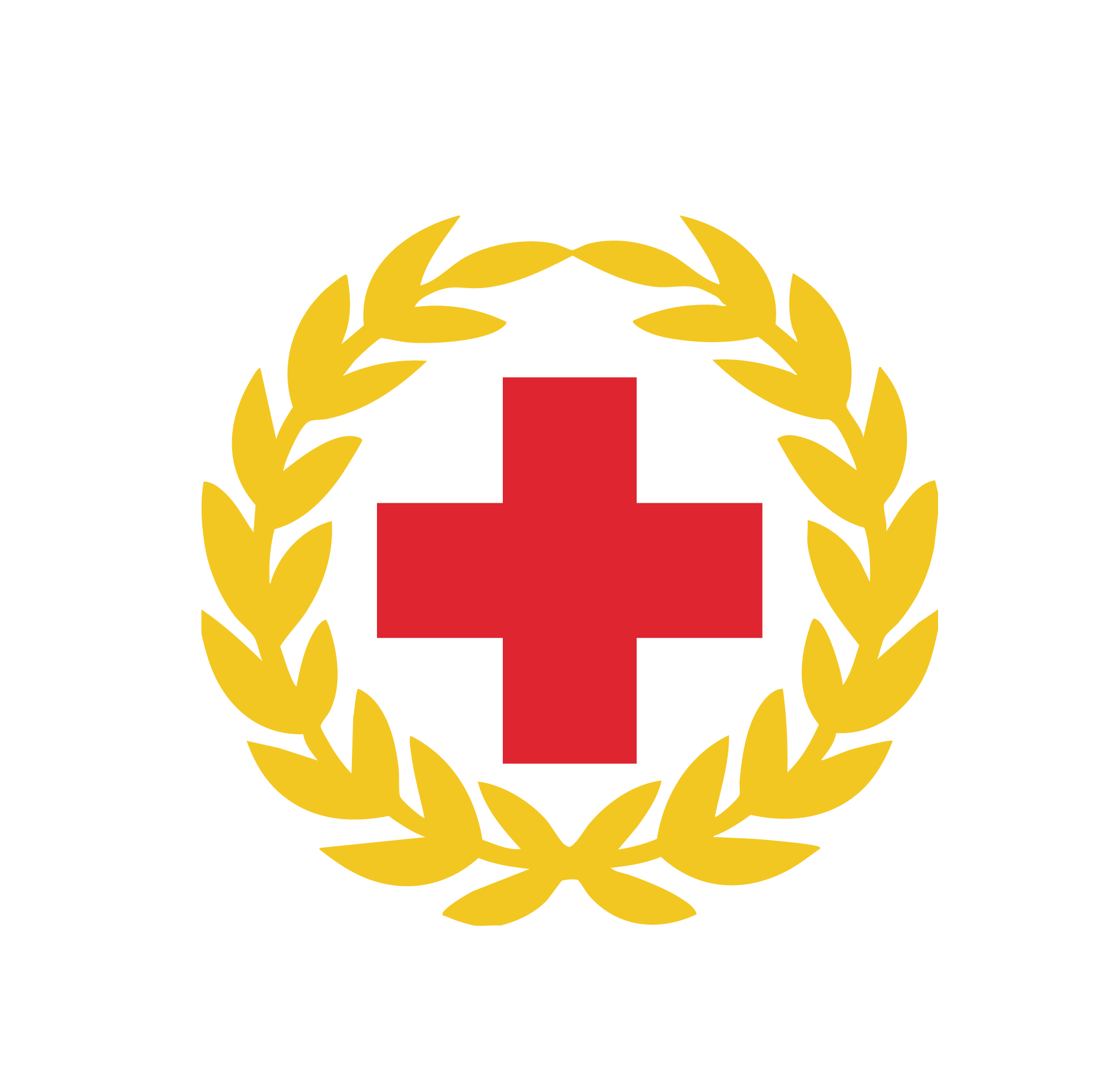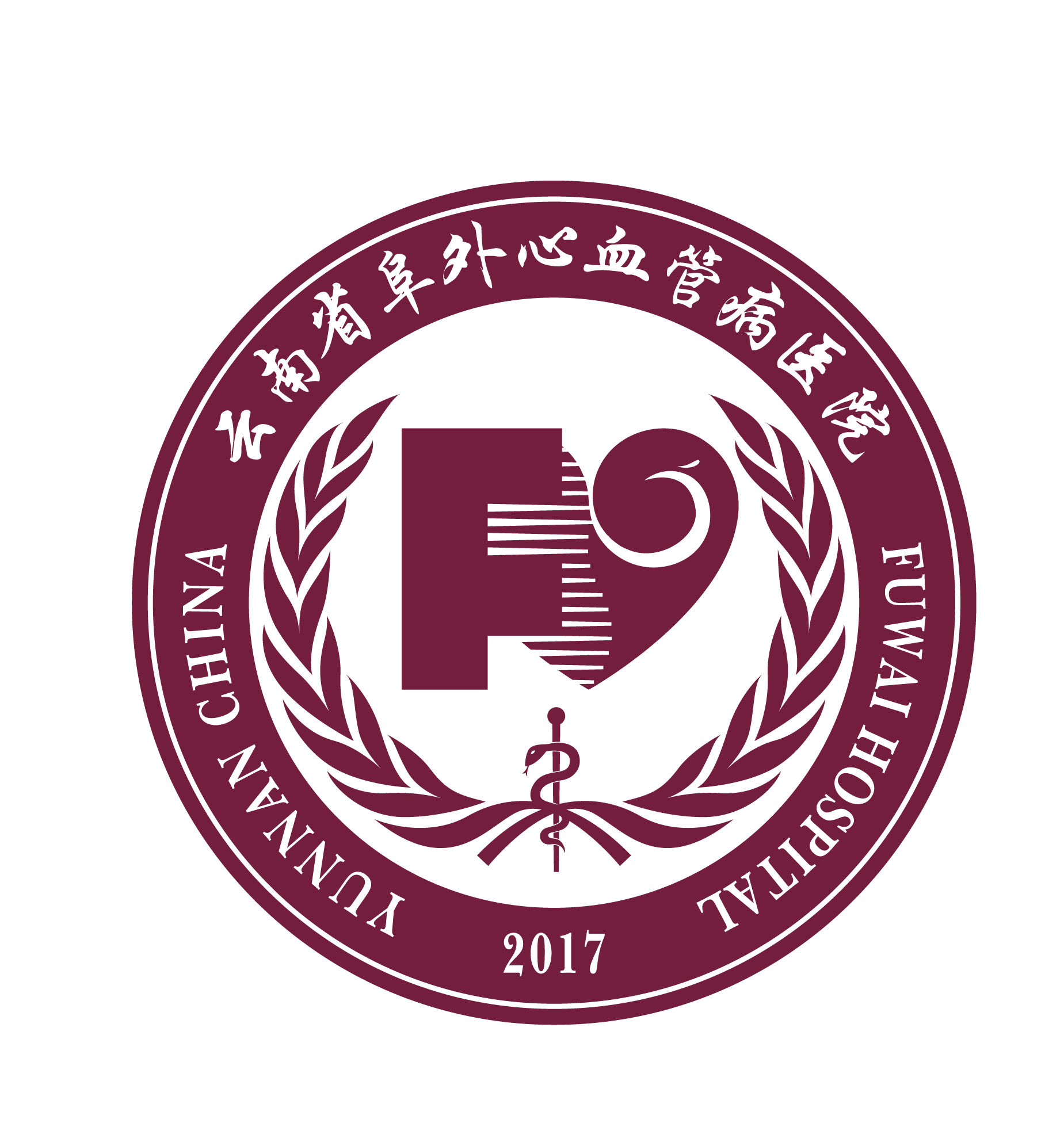葛均波:介入心脏病学新技术任重道远
时间:2014-07-22
浏览量:2015
《门诊》杂志特别邀请OCC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葛均波教授,围绕介入心脏病学领域新进展及大会亮点介绍给广大读者。
《门诊》:今年东方心脏病学会议特别增设了心脏急症论坛,请问其初衷是什么?目前我国CCU的建设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每年OCC会上您都会带给广大参会医师惊喜,能否透露一下今年OCC手术转播的亮点?
葛均波院士:目前我国对心脏重症监护室(CCU)建设存在认识方面的问题,首先对于该疾病的重视程度不够;其次还牵涉到患者医疗费用支付的相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很可能无法得到最优化的治疗,临床获益大大降低。大会组委会特别在本届东方心脏病学会议上增设了心脏急症论坛,目的是希望能够提高广大医师对心脏急症的重视,推进我国CCU的建设,使心脏急症患者得到最优治疗。
大量临床研究结果证明,冠心病患者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时,尽早开通病变血管能够有效改善患者心功能水平及预后,降低患者死亡率。但是由于患者自身延误、转运急救系统不力以及院内急性心肌梗死救治流程不完善等原因,许多患者由于时间延误错过了治疗窗,出现大面积心肌梗死。由此引发心脏收缩时丧失活动能力或呈现反常运动,进而形成室壁瘤,而室壁瘤容易诱发血栓形成并导致心脏重构。虽然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切除室壁瘤,但部分患者不愿意或不能耐受外科手术治疗。
今年OCC手术转播计划推出一项新技术-经皮心室重建术(Percutaneous Ventricular Restoration,PVR),通过在患者心脏内植入左室隔离装置,减少患者心脏的容积,“降落伞”随心脏收缩,代替瘢痕心肌,有效改善心力衰竭的临床症状,增强心脏做功能力。
中国患者比较排斥有创的外科手术,这种观念促使许多患者希望接受微创手术,它也是我国微创技术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而该项技术手术风险相对较小,临床效果非常显著。如果能够得到推广,可以让很多心肌梗死并发室壁瘤的患者得到显著获益。
《门诊》:经导管心脏瓣膜置换术是近年来学界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去年TCT会议上公布了CoreValve的临床试验,之后正式通过FDA批准;今年ACC会上则分别公布了CoreValve的随机对照试验和STS/ACC TVT真实世界注册研究,无论是临床试验还是大样本真实世界注册研究均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对此您有何评价?另外在您看来,TAVR新植入起搏器比例较高的情况能够改善吗?
葛均波院士:今年ACC会议上公布了两项实验,分别是CoreValve的随机对照试验和STS/ACC TVT真实世界注册研究。CoreValve的试验结果证实TAVR组一年全因死亡率显著低于外科手术组(14.2% vs. 9.1%,P=0.04)。对于这类非外科适应证的患者,CoreValve瓣膜支架增加了介入医师的信心,它能够避免患者因外科手术引发的出血、感染、输血、麻醉及大型创伤等风险。本研究结果为经皮瓣膜修复领域今后的快速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针。
我们中心曾对CoreValve瓣膜支架系统进行相关研究和临床实践。CoreValve瓣膜支架系统为自膨胀式,患者植入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患者心脏瓣环撕裂的几率较小。但是它也存在一个缺点,相关数据显示5%~40%植入CoreValve瓣膜支架系统的患者需要安装起搏器,导致患者的手术成本大幅增加。如果我国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在TAVR术后最高有40%需要安装起搏器,无论是医保还是患者自身都无法承受如此昂贵的医疗费用。因此需要进一步权衡应用CoreValve瓣膜支架系统的得失。当然,随着我们植入技术的改进和对局部解剖的了解,并发症和起搏器的需要也逐步减少。
《门诊》: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TAVR高昂的费用可能是阻碍其在我国得以发展的最大阻力。作为最早在国内开展TAVR的专家,您认为国产化是否是一种选择?
葛均波院士:TAVR的医疗成本确实较高,因为不仅要考虑其材料成本,相关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该项技术及产品的前期研制,作为投入的回报,企业希望通过产品销售获得一定利润也无可厚非。如果研发成本无法收回并盈利,那今后就不会再有企业进行科研创新。
问题在于,如何让企业在合理的范围内盈利?这是科学家和政府应该达成的共识。记得进口药物洗脱支架刚刚进入中国时,一枚支架高达38,600元人民币,许多患者难以承担医疗费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国产企业也逐渐开始研制药物洗脱支架。早期的国产支架借鉴模仿了国外产品的特点,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吸收并消化,最终转化为自主创新产品。随着技术不断改进和完善,EXCEL支架、Firebird支架及Partner支架三种国产药物支架相继上市并迅速占领国内市场。目前一枚国产支架大约10,000元,超过70%患者都选择国产支架。更重要的是,国产支架不仅价廉而且物美,与进口支架相比并不逊色。
从国产支架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学习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走国产化之路是完全可行的。虽然TAVR等新技术在国内起步不久,但相信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门诊》:您曾经提及自膨式人工瓣膜存在打开后不可回收的问题,目前是否存在新技术能够进一步优化这一操作?您认为新技术的亮点在哪里?
葛均波院士:球囊扩张式的Edwards瓣膜支架系统和自膨式的CoreValve瓣膜支架系统植入后要重新调整位置非常困难,操作不当可能导致患者主动脉撕裂。并且一旦完成植入,即使造影发现有返流,介入医师也很难找到补救措施来纠正。
目前有两种新型瓣膜支架系统获得了欧洲CE认证,一个是Boston Scientific Lotus Valve System,另一个是Direct Flow Medical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System。
这种新型瓣膜支架既不是自膨胀式也不是通过球囊扩张,它有两个瓣环,心脏瓣膜位于两个圈之间,如果将支架的两个环扩张起来,观察到没有返流出现,就可以释放固化剂将其固定。而且不像自膨式瓣膜支架打开后不可改变,这种瓣膜支架的位置能够进行调整。如果瓣膜支架系统植入的位置不理想时,可以取出后重新定位。
这一新技术为心脏瓣膜病患者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手术成功率,还能够减少返流发生率,降低起搏器使用率,全面让患者获益。
《门诊》:新技术的开展往往难以一帆风顺。TAVR在我国如此,RDN更面临着能否存续的境遇。在SYMPLICITY HTN-3公布之初,您在接受我刊专访时就表示试验的失败可能与未能完全有效消融有关。澳大利亚Murray Esler教授与您有着类似的观点,并表示对于RDN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然而限于利益趋向等因素,RDN的研究可能会进入低谷期。即使在消融导管等方面进行改进,如果没有非常有说服力的RCT研究,可能无法重新建立起对该技术的信心。您认为,我国在这一技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暂缓等待国际的进展?
葛均波院士:我一直在思考SYMPLICITY HTN-3试验结果无效的原因是什么。可能由于导管的原因,完全没有将肾神经消融,或者消融了一部分但没有彻底消融肾脏神经。研究过程中很多因素可能影响最终的试验结果。虽然研究失败了,但是我相信肾神经消融术对治疗或者控制减缓肾脏纤维化和微量蛋白尿是非常有效的,该研究失败可能与导管和术者操作存在一定关系。
SYMPLICITY HTN-3试验显示,该研究设计应该纳入难治性高血压患者,而实际入组标准是患者服药2周后血压不能控制的人群,显然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难治性高血压的人群,因此该研究前期患者筛选不严格可能也会影响最终结果。针对RDN的研究,无论国内外今后都会继续进行相关研究,包括导管的改进等,新的研究结果值得我们期待。
《门诊》:我国2013年PCI例数已超过45万例,县级医院开展PCI术也方兴未艾。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又担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在带领推动我国最新技术发展和全面提高基层心血管诊治水平方面是否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
葛均波院士:我们应该从西方医学界曾经走过的弯路中吸取教训。在上世纪80年代,临床上很少遇到心肌梗死患者。当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心内科大部分住院患者为高血压、心力衰竭及早搏,很少有心肌梗死的患者。如今,我国每年心肌梗死患者的数量都在增加,预计在未来数年内,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会呈现爆发性增长趋势。这一趋势向我们提出了问题:是让其自由发展再控制还是积极进行早期预防工作?显然预防比治疗更为重要,投入小收益大。但是预防工作并非医院能够承担,因此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投入资金,全面主导疾病预防工作。
《黄帝内经》说:“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目前预防工作不力,与目前卫生政策有关。按美国三亿人口每年大约100万例PCI手术推测,中国冠心病患者数量在未来数年可能达到300万例,年轻人群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除了工作压力大,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疾病发生。疾病的预防工作非常重要,纵观历史,人类平均寿命的增加不是因为高端的技术,而是基本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20世纪全球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有效控制了霍乱等流行病的传播,整体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因此在我看来,全国范围的心血管疾病防治工作并不比新技术的开展容易。需要通过给政府建言等方式,改进公共卫生政策和管理措施,虽然任重道远,但我们责无旁贷。
上一篇: 年轻人也会心梗,警惕心梗“小苗头”
下一篇: 糖尿病人每天饮食量如何算?

阜外院训
敬业 · 仁爱 · 求实 · 攀登
军队文化
对党忠诚,信念坚定,听党指挥,从大局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注重团队协作,组织纪律严明
协和文化
协和精神:严谨、求精、勤奋、奉献思想内核:崇尚科学、崇尚知识、 专业态度和专业精神表现方式:凝重、内敛、不张扬、重视口碑效应
精英文化
始终以成为行业内精英医院为奋斗目标以【培养国家级心血管病专家为己任】